
![]()
每一段赤手空拳的青铜时代,都是王者们的螺旋升级之路。艰难困苦往往是成长和人生蜕变的机会,这个世界没有白吃的苦,也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我的青铜时代】栏目,关注神经介入医生的成长,从大师的故事中,思考、构建自己的故事。

一杯咖啡,余香渐散后,一段青涩的往事慢慢浮出水面。
2月10日,在海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上海长海医院)会诊中心,身穿白大褂的刘建民教授匆匆赶来,在接受脑医汇-神介资讯采访前,他静坐一旁,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过后,慢慢放松了自己。在谈及自己的最新研究——ENCHANTED-2/MT时,“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自信与意气风发倾泻而出。但当把时间的进度拉到刘教授的青铜时期时,谁又能想到现在闪闪发光的刘教授,也曾夜半躲在无人的角落“哭鼻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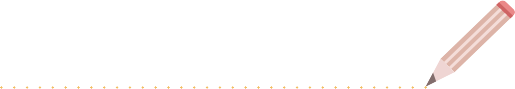
开眼看世界:原也是池底蛙
时间倒退回30多年前,那时不仅刘教授初出茅庐,我国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也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
1979年,在军医父亲身体力行的感染下,刘建民教授在成功挤上千军万马的独木桥后,填报了医学院,并按部就班的跟着学校安排完成学业,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在1992年。那一年,刘建民教授在武汉军区总医院(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马廉亭教授组织的学习班上,第一次接触到神经介入,由此打开了神经外科新的天地。

当时中国的神经介入也才刚刚起步,全国只有少数几个医院尝试开展介入治疗且全国只有几个人探索研究,由于当时的影像设备及器械较为“原始”,很多设备、器械、材料甚至都要自己制作,能够开展的介入治疗也是屈指可数。
因此,神经介入这一“洋玩意”不仅普通大众不知所以,甚至当时大多数的神经外科医生也是闻所未闻。
水到渠成,介入思想萌芽扎根
出于想用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解决病人问题的刘建民教授,在医学的科室方向上选择了外科,而在当时难度最大的心胸外科和神经外科中,又选择了挑战难度更大、空白更多的神经外科。然而真正深入研究神经外科相关疾病,才发现越是了解越是想改变。刘建民教授回忆:“从1992年开始,我已成长为主治医生了,科室里的脑血管病手术越来越多,但手术仍以开颅手术为主,且因手术困于条件,术后效果非常有限。那个时候我接触到了神经介入,其实我还看不清楚整个脑血管病治疗的未来,但既然这个方法(开颅手术)还不够完美,就要想去尝试新的方法(介入治疗)。”
你知道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年轻!因为年轻可以去做各种尝试,敢于去实践各种梦想。
此后,他积极主动关注神经介入方面的信息,并陆续与我国第一代神经介入开拓者吴中学、凌锋等教授结识,更是在1997年,作为客座副教授前往日本的大阪市市立大学医学院交流学习。在日本的交流学习中,刘建民教授首次接触到了现代的神经介入治疗,见到了双C三维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3D-DSA)和电解可脱弹簧圈(GDC),并为之着迷。为此,他不知不觉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脑血管病上,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神经介入上,也因此自然而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当中。
真正的蜕变是在参加完英国牛津大学Byrne教授主办的颅内动脉瘤介入学习班后完成的,在那里,刘建民教授对神经介入治疗的理解更为深刻,并于此后萌生了如何缩小国内外神经介入水平的差距、如何提高国内医生对神经介入技术的认知、如何快速推广普及以及推动相关应用的同质化水平的想法。
背水一战,踏平一切困难做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进行第一例颅内支架,后续几年间得到90%以上的反馈都是质疑,甚至认为我们在不负责任、在乱做。
1929年,德国一位年轻的外科医师——沃纳·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一根输尿管经静脉插入自己的心房,拍下了一张X光照片。就是这个当时看来实在过于疯狂的举动,不仅为他个人赢得了一枚耀眼的诺贝尔奖(195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后来改良该技术的美国外科医生André Frédéric Cournand和Dickinson Woodruff Richards一起分享),也宣告了心血管介入治疗时代的到来。
相似的故事不断发生,在神经介入领域也是如此,所有这些烙在刘建民教授记忆中栩栩如生的故事也影响到他自己的思考与实践。二十多年前,刘建民教授进行第一例颅内支架治疗时,作为一个在学术圈籍籍无名的年轻人,就遭到了学术界的激烈质疑。当时,把冠脉支架引入到颅内是非常艰难的,尽管国外已有个别医生开始尝试,但国内依然还拿颅内梭形动脉瘤没有办法。基于此,刘建民教授就想去尝试这一新方法,然而历经一年,每每提起,不是病例被否决,就是因没有文献报道等支持而治疗方案被毙。
直到2000年,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刘建民教授事先把所有的文献查好,又把支架治疗以后可能面临的问题准备妥当,然后才同医院科室的主任、教授们汇报、沟通……说服,接着做好患者沟通工作,终于成功开展了中国第一例颅内支架成形术。
该例颅内支架成形术的成功实施,意义重大,在国内外争相被报道。然而事情的结尾并非是鲜花和掌声,刘建民教授表示:“我进行第一例颅内支架,后续几年间得到90%以上的反馈都是质疑,甚至认为我们在不负责任、在乱做。”
事实证明,颅内支架成形术现已成为整个神经介入最重要的技术。那位当时已别无他法的患者在刘建民教授等医护人员的见证下,不仅举办了自己的新生20周年仪式,而且还愉快地约定了30周年庆典。
“不要担心自己成为异类,在大家习以为常的世界里去看到自己的不足,勇于尝试,不怕失败,做不一样的事情,一定会收到方方面面的质疑和挑战,但科学的进步发展本就来自于质疑,如果没有‘异想天开’,没有创新,科学也不会进步”,刘建民教授如是说。

打破思维定势,直面质疑
采访时,刘建民教授分享了他女儿的一则趣事。周末他带女儿去周边攀岩,因为年纪较小,最初尝试了几下很快就自己下来了。于是刘建民教授尝试给女儿定一个小目标,鼓励她努力攀到中间的位置,女儿坚持了一下,居然轻松地完成了爸爸给自己设定的这个目标。休息一会儿后,接着他又鼓励女儿再攀一次试试,但是这次并没再设置新的目标,结果女儿顺利地攀到了顶点。其实,你比别人眼中的自己以及自己想象中的自己更强!
不给自己设限,全身心地投入是刘建民教授最大的感悟。
哪怕我们的探索是错的,但重要的是我们敢于开始探索。
仍旧把时钟调回二十年前,颅内支架成形术在国内还是一项新鲜事物,刘建民教授满载着他个人成功的经验和成果,在北京一场大型学术会议上分享该项技术。当时,与会的一位老专家给了他当头棒喝:“你凭什么这么做,有什么依据?哪本教科书教你的?你这么做符不符合伦理?”会场鸦雀无声。
当时的刘建民教授才40岁,于学医者而言,还属“小年轻”,而这样的年轻人要在国内专家荟萃的学术大会上直面权威毫不留情地质疑,可谓“亚力山大”。
刘建民教授的回答铿锵有力:“你说的特别对,你看西医来自于西方,我们今天所有的体系都是来自于西方——我们的设备、技术、知识、材料都来自西方,我们的临床实践也是跟着西方走,西方说做你就做,西方说No你就不能做,西方不说我们就等,对不对?但是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也经历了20多年了,现在我们的材料和国外同步了,我们的医生国际交流走出去、引进来,我们的眼界也不一样了,我们的知识有互联网也同步了,所以当我们面对病人的问题时,我们具备了和西方人一样去思考、去探索、去尝试的能力。那为什么西方人可以用新的技术去探索、去突破、去救治那些没有办法的病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探索、去突破、去救治我们的病人?哪怕我们的探索是错的,但重要的是我们敢于开始探索。”
这一次,刘建民教授收获了他人生中最热烈、最长久的掌声。
完美主义者,把自己逼到“哭鼻子”
刘建民教授在出国以后,尤其在参加了LINNC和WFITN后,对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认识得愈发深刻。与众不同的是,刘建民教授此时想的不仅是自己要学好新技术、新理论,他还在思考,如何在中国也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从而把国际上有关脑血管病介入治疗的最新理念、知识、技术,以及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尽快地传递给中国更广大的医生。
由此,2000年前后,刘建民教授在已经组织了多个神经介入学习班之后,在周良辅院士、刘承基教授和朱诚教授等老专家的鼓励下,在吴中学、马廉亭、凌锋、焦德让和李铁林教授等中国神经介入前辈的支持下,于2001年10月25-29日,在长海医院科技楼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了首届东方会(OCIN)。但是从0到1,困难重重。
根据刘建民教授的回忆,他当时就意识到,仅凭他个人的成长、理念的更新、技术的提高、经验的积累,去普及和推动中国神经介入事业仍是非常有限的,必须要让全世界和全中国的专家一起来交流分享。
另一困难则是中国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办会模式:报数字、排座次……,诸如此类,真正学术交流的整体效率却很低下。刘建民教授决心,OCIN必须要做些什么改变。
因为年轻,因为有很多阻力,开东方会我都哭过鼻子。
为此,他在首届东方会上,凡事亲力亲为,强调会议以学术为重,打破“因讲者定题目”的传统;会议安排上不接、不送、不设主席台;严格限定发言时间,提前两分钟进入倒计时,倒计时结束时分享自动停止等。这一系列的“颠覆性”办会模式,可谓将行业同仁都“得罪”了。在被问及当时是否会因为这些规则担心专家同仁不给“面子”不参会时,刘建民教授自信表示:“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的整个氛围中,所有的东西都在改变,只是快和慢的区别,这是大趋势。”

一切从学术角度出发,奠定了OCIN二十多年以来一以贯之的基调,也为初生的OCIN带来了更多的阻力。刘建民教授直言:“开会前一个星期,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因为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把控。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希望把东方会办成和我在国外参加的学术会议一样,这就要求我们整个组织策划,从首先确定最新进展,再去联系邀请这个领域全世界真正权威的专家,然后编排日程、实施细则,全要精心安排。因为年轻,因为有很多阻力,开东方会我都哭过鼻子。”
即使困难重重,刘建民教授在回忆起东方会办会艰难时,仍然坚定认为创办东方会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情。
生命在于“折腾”,跳出舒适区
除了死亡是注定之外,生命其实有无限的可能,“奇迹”每天都在发生。
刘建民教授就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不太喜欢在一种状态下反复的去重复,他更喜欢跳出“舒适圈”,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尝试一些新的事物,不断攀爬新的医学高峰。
采访中,刘建民教授曾问过:“你知道人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是年轻!因为年轻可以去做各种尝试,敢于去实践各种梦想。”他不仅这么认为,他也在身体力行地践行。
作为东方会的创办者,东方会已成为国际脑血管病治疗领域最权威的大会之一,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站在神经介入的峰顶,以脑血管病中心主任和创伤中心主任的双重身份,又一次面对质疑,分享关于头颈部创伤与血管创伤的微创介入治疗的创新理念,并把介入技术与早期血管评估及干预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刘建民教授的讲述中,每每当他通过现有的治疗方法无法使病人获益时,他都更愿意为病人、为自己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努力获得更好的结果。这种创新的价值,以及内心成就感创造的愉悦,对他而言是无与伦比的。
不要担心自己成为异类,在大家习以为常的世界里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一定会收到方方面面的质疑和挑战,但科学的进步发展本就来自于质疑,如果没有‘异想天开’,没有创新,科学也不会进步。
说给“青铜时代”的你
——刘建民教授的经验之谈
人不能脱离环境而言。对于当下年轻人想要追逐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收入、更理想的工作,刘建民教授表示非常理解并支持。想要达成这些目标,刘建民教授认为,不妨在自己热爱的某一项事业上或某一个点上深耕精作一番,只有不计回报,不计较任何东西的全身心投入,才能在自己所热爱的领域里打好基础,继而发光发热,有一览众山小的机会,而不是汲汲营营在山谷里为选哪一块石头为难。
只有站得足够高,才能知道方向。
专家简介
刘建民 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导
脑血管病中心主任,战创伤中心主任,全军脑血管病研究所所长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
国家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工程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卒中中心管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卒中专科联盟副主席;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副会长;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常务委员;全军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世界神经介入大会(WLNC)执委;2011世界颅内支架大会(ICS)主席;2016/2021 WLNC主席;东亚神经介入大会(EACoN)主席
脑医汇-神介资讯主编
“

”
扫描上方二维码
进入刘建民 教授学术主页
END
点击或扫描上方二维码
查看更多“介入”内容







